(本文转载自“博智宏观评论”)
2021年11月10日下午,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增强中国城市发展韧性”研讨会于线下线上同步召开,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晓林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我有两个题目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是特大城市风险和韧性建设;一个是我们团队长期做的韧性社区建设,因为社区是城市发展的底座。我把这两个穿插到一起,但是重点讲特大城市基于韧性建设的行政区划。
特大城市是风险容易发生和扩散的场域,我们国家(大陆)现有21座特大超大城市,这21座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17279.52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0.18%,但是GDP占全国32.9%。在未来一段时间,武汉等城市有可能进入超大城市序列,石家庄、昆明、苏州等一些城市会进入特大城市行列,未来特大城市的量、容都会不断扩大,GDP总量也会占全国4成以上甚至5成。这决定了特大城市在国家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版图上占有极端重要的位置。
我们在疫情期间进行了全国8000多份问卷调研,统计发现社区层面有几种风险是居民常见的、有深切体会的,特别是电梯的风险,问卷统计显示近三个月内遭遇过电梯故障的人占了样本的36%左右,其它在社区范围内容易发生的一些风险,比率比较高的为交通事故、住处被盗等风险。
在处理、应对、防范风险的时候,社区韧性的一些指标不是特别强,有几方面的表现:一是社区应急管理权责不清晰,相关政策没有界定基层村居组织的权责。二是基层应急管理体系不健全,我们在疫情期间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样是8000多份问卷),42.11%受访者表示社区没有应急预案。通常是,平常有应急演练的社区,居民对应急反应的效果评价好一些,没有演练的,效果则差一些。三是社区应急资源短缺,普通社区配备相应救灾物资满分2分,得分1.1分,不及格。四是社会风险防控压力大,现有社区人口规模偏大,有的居委会平均一个人对接3000多人。五是居民参与疫情防控不足,全国只有3.44%的居民参与了社区防疫志愿者活动。
那么,特大城市的情况如何呢?首先要说明一下,有人研究说作为城市规模的函数,大城市的人口增加100%犯罪率可能增加120%,这是城市规模跟风险间的关系。通常的情况是,我们的城市规模和体量普遍偏大,这样一来,很多人把空间重新划分或者疏解人口作为控制风险的手段,但恰恰忽略了韧性这个中介变量。当然,韧性的反面就是脆弱性,我们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减少脆弱性是一个人权问题,而减少风险则不是。对风险的事后弥补,往往并不能成功地减少脆弱性。
现有特大城市风险是属地化防控的方式,不管是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还是落实到地方层面具体的管理办法,不但规定了县级以上政府管理部门的权责,也把乡镇、街道办、社区都纳入到风险防控的属地范围内。也就是说,谁出了问题谁负责,谁出了问题不但要负责上报,还要负责解决。比如大家平常并不知道社区还要承担这样一些风险防控,例如,要经常排查风险漏洞,比如安全生产,每年到了冬季要排查燃气是否安全,地面井盖是否安全,出了问题,居委会的人也要受问责。在属地管理的防控方式下,不管是乡镇街道还是社区工作人员都面临一票否决的问责约束。
属地责任跟城市韧性之间往往存在“非适配性”,它本身是脆弱的。有几个表现:
一是,行政区和管辖区不统一的风险,长臂管辖存在管理真空。不同城市有相应的插花地,就是飞地,有的城市中心没有土地了,到郊区划一块土地,谁去买房,户口就归市中心城市管,享受上学等服务,但是人住在郊区。那么,风险来了谁管,行政区所在的区说户口不在这里,户口在的中心城区又无法管辖,就容易成为三不管的地带。在疫情期间,插花地的风险表现尤其大,有的地方都出现居家老人伤亡情况都不清楚的情况。
二是,功能区跟行政区之间也存在不统一的风险,比如说2013年青岛油管爆炸涉及到本来是中石化所管辖公司安全生产的问题,结果还是要问责当地所在的行政区管委会,包括街道办主任被免职问责。如果街道办主任去承担风险防控的责任,公司自身也负主要责任,所以互相交叉,责任模糊。2015年发生的天津港大爆炸,天津市港口是交通部管理,但是当地政府担负属地责任,属地要查港口,也面临责任交叉,对它没有什么制约,不但要问责天津港、交通部管理部门,也要问属地责任。但是当时责任交叉就形成了安全隐患。
三是,既有的属地管理无法应对风险跨区域的溢出扩散效应。风险灾害并不局限于某一个人为所划的行政边界,一般都会产生灾害链,它会溢出我们的行政边界,不受物理空间限制,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风险,随着人口流动跨域传播的风险特别大。我们要应对这样大的疫情和风险就需要跳出行政区域,需要全国全省各地市对疫情发生区域的对口援助,否则依靠自己无法完成。
与此同时,我们的行政区域规模普遍太大,风险治理就会面临超载的问题。我们国家跟西方国家城市不太一样,西方国家城市大多是城市群,大家虽然在一起,但是依靠高速公路或者轻轨、地面有轨电车来连接大小城市,但是我们国家动不动就合并,越大越好,规模非常庞大。我去过一个最大的街道人口超过100万,这在西方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我们国家最大的单体小区入住人口达到50万,在贵州花果园小区,最大的社区是北京回龙观、天通苑96万人口。那么疫情来了,风险来了到底怎么弄。一般是一比一千人社区服务统筹着,一比一千人要提供什么样的风险防控工作、责任呢?包括综治维稳、城市管理、流动摊贩管理、流动人口管理、物业纠纷、安全生产检查、禁毒宣传等等所有都归他管,出了事儿就问责。实际上他管不了,也没有这个业务能力。比如检查电梯安全,把责任交给社区,社区没有这个专业能力,而且还有疫情防控期间要消毒、检查工作,他也没有这个专业能力。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我国规定消防站布局在5分钟内可以到达,但是有的超大街道和社区超过15分钟。紧急避灾的疏散场所步行大约10分钟内可以到达,但是有的街道和社区要超过15分钟,有的甚至没有这样的设施。这样的话,风险来了就是出人命的事情。我们研究了一下社区要承担29项安全检查,这是北京一些由社区承担的工作责任,几乎无所不包,基层社区的工作人员压力很大。
最近,我们在做一个课题,研究特大城市行政区划如何应对城市风险,支撑韧性城市建设。我们提出三区三圈层的建议。三区就是社区、政区、跨区的三圈空间治理模型,实际上也是为了推动韧性城市建设。
一是,在社区层面基于人居安全的需求营造安全场景,因为社区恰恰是跟人类生活最密切的、最基层的单元,是生活区域,而我们要承担城市风险大多要靠社区城市基层的底座完成。安全风险的清单,整个社区15分钟生活圈内到底有哪些风险漏洞,应对这些风险时哪些环节是脆弱的,风险一旦来了,会形成怎么样的情景,基于这样客观和主观的想象来营造安全场景,进行总体的打造。这是场景的应用程序,一旦风险来了怎么启动,怎么防控,程序是怎么样的,都要设计好。
二是,行政区划层面,建议基于人口密度和规模做好行政区划调整。现有行政区划都是过大的,而且都是块状的,一般哪里资源好哪里资源不好,依靠行政边界就可以看得出来,把优势资源锁在少数中心城区里。建议未来有必要的情况下把块状行政区划向扇形行政区划调整,使得中心城区获得腾挪的空间,也使得中心城区抗风险优质资源向外围扩散。这可能是有利的。
三是,在跨区层面要基于安全风险类型推动跨域治理,因为风险来临后,靠单个城市应对还不太足,特别是应对战略风险、特大风险的时候,比如说新冠疫情风险来了以后,单纯依靠本地行政力量是很难完成的,这就需要跨区域协同,在城市群内协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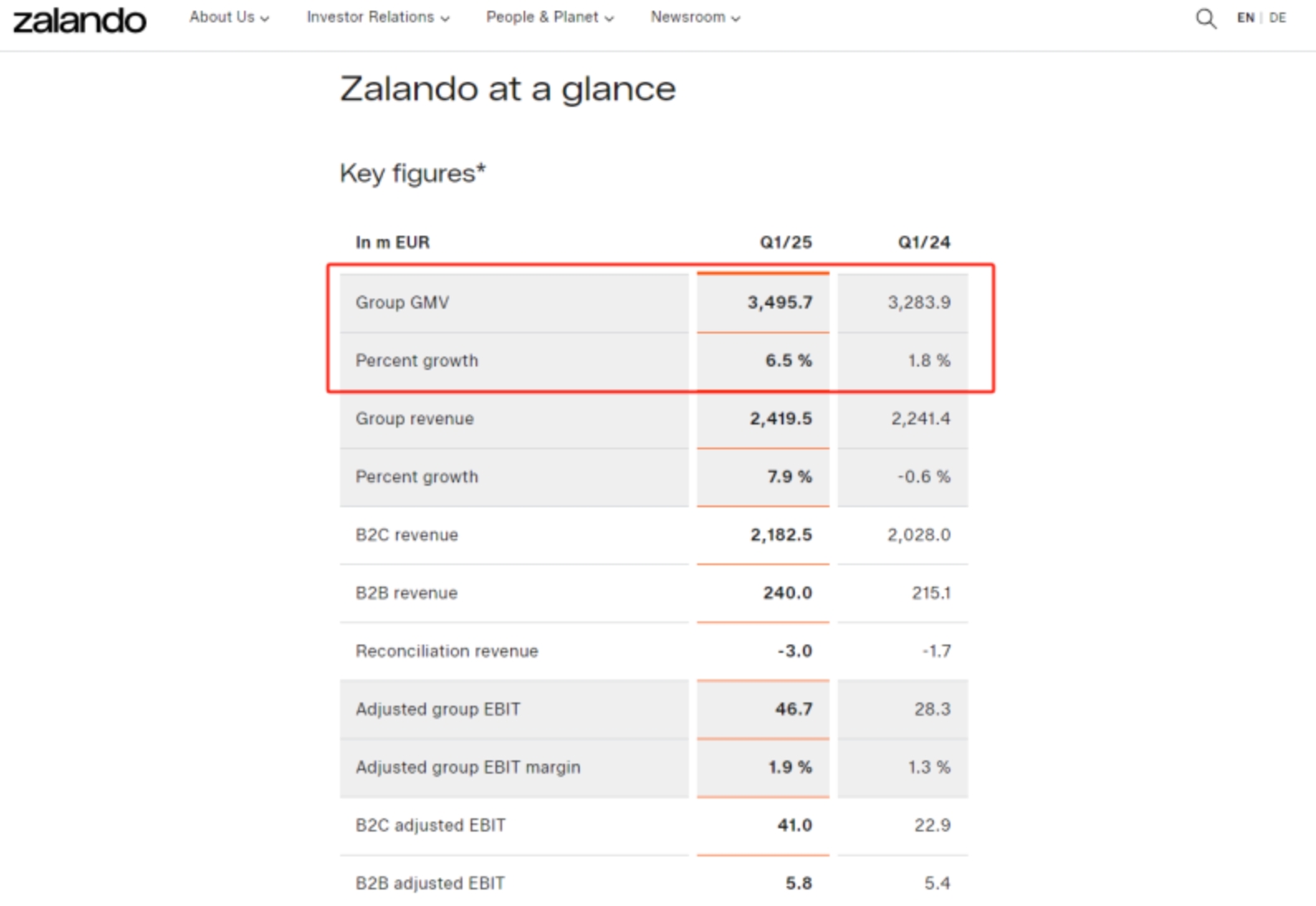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