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冲击’之后,我们是否还会面对‘拜登冲击’?”
在为即将出版的高海红教授新著《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一书所作的序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抛出上述疑问。在他看来,“如果以往的经济理论还有存在价值,我们就不能不对美国的极度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冲击深感忧虑。”
在回顾、梳理了自18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沿革之后,余永定剖析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指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根本特征是美元本位,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信用由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弊端显现,存在通货紧缩倾向、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三大缺陷,其背后的根源是:作为一种国别货币的美元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
就中国而言,余永定强调,中国不仅需要在现存体系中趋利避害,而且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海红2021年新著《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经济科学出版社)所做序言,原文经编辑后收录于《新金融评论》工作论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受版面所限,本文略去注释和参考文献,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全文。
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与中国的定位
——评《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
文 | 余永定
高海红教授是“60后”国际金融专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的创建人,一直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国际金融研究的领军人物。我与高海红教授共事26年,经常同她探讨国际金融问题。高海红教授概念清楚、思维缜密、视野开阔,在同她的学术交流中我受益良多。高海红教授严谨治学和低调谦虚受到学界同侪的广泛好评。
高海红教授的新著《变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 理论与中国实践》是她长期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总结与概括。该书内容包括了中国学界在过去几十年中所讨论过的与国际货币体系相关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由于我们是长期合作者,我十分认同她在书中所阐述的主要观点。如果有什么分歧的话,很可能是我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更极端一些,而她则坚持一种更为平衡的立场。
中国的开放过程很大程度是加入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接受者而不是建立者或改革者。但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方面,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美元外汇储备国(有时被日本超过)、世界最大债权国之一(2019年拥有2.3万亿美元海外净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第三大股东;人民币国际化也取得长足进步,人民币成为IMF的特别提款权(SDR)篮子的第三大构成货币。中国有权要求国际货币体系能够更多倾听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尽管美元始终是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本位货币,美国政府却越来越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特朗普执政时期所实施的政策更是公然打出“美国第一”的旗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必然会动摇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如果以往的经济理论还有存在价值,我们就不能不对美国的极度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无限量货币宽松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冲击深感忧虑。在“尼克松冲击”之后,我们是否还会面对“拜登冲击”?
改革开放之前,无论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何种动荡,中国基本上不会受到严重冲击。现在,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最重要参与者之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任何动荡和变革都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造成难以估量的重要影响。中国不仅需要在现存体系中趋利避害,而且必须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金融学者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沿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可供选择的改革路径已经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尽快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的国际货币体系危机应对预案和中国自己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和路线图。我相信,高海红教授的新作将对这一努力做出重要贡献。
国际货币体系沿革:
从金本位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必须能够行使两大功能:提供足够的国际流动性(liquidity)和调整(adjustment)国际收支平衡。而为了能够行使这两大功能,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必须首先回答三个基本问题:选择什么货币作为本位(standard)、如何决定汇率以及如何管理资本的跨境流动。对这三个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定义了不同的国际货币体系。
金本位制
18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货币体系以黄金为本位。在金本位下,一国货币和黄金按货币的法定含金量自由兑换,黄金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一国黄金产量和贸易盈亏决定黄金储备量(存量),而后者则决定该国货币发行量。换言之,在金本位下,货币发行量存在由黄金储备量决定的上限和下限。在金本位时期,英国在绝大多数年份保持贸易逆差。但由于投资收入始终是顺差,直到1930年代之前,大英帝国一直都是经常项目顺差国。由于黄金储备充足,英镑成为金本位下的主要国际支付手段,英格兰银行成为世界的银行。当时的金本位制实际上也是英镑本位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暂时中止实行金本位。按英镑和美元的法定含金量,战前英镑对美元的汇率是1英镑兑换4.86美元。由于战争期间英国通胀严重,而美国的通胀较轻,战争接近尾声时,英国政府让英镑对美元贬值到1英镑兑换4.7美元。1920年外汇管制解除之后,英镑对美元贬值到1英镑兑换3.44美元。在战后一心希望恢复金本位的英国政府实行了货币紧缩政策。在战后的两年之间,英国信贷增速下降了20%,物价下降了34%。1922年,在付出失业率高达14%的代价后,英镑对美元汇率回升到1英镑兑换4.61美元。1925年丘吉尔宣布恢复金本位,同时让英镑对美元汇率保持在战前的1英镑兑换4.86的水平上。
理论上,金本位具有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遏制通胀或通缩的自动调节机制。例如,如果国家A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导致物价上涨,相对物价稳定的国家B,A对B出现经常项目逆差,黄金由A流入B。为保证金本位要求的货币兑换黄金比率不变,A必须紧缩货币供应,而B则可以增加货币供应。其结果是:A物价下降、出口增加;B物价上涨、进口增加。这个调整过程要一直持续到国际收支恢复平衡。在此过程中,A的通货膨胀被输出到B。
金本位得以实行的前提条件是各国都遵守“金本位的游戏规则”。如果B担心本国物价上升,在黄金流入的同时,阻止本国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则金本位的自动调节机制就会失效。以英美两国为例。战后,当英国采取货币紧缩政策以恢复金本位的同时,美国拒绝执行更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英国黄金储备不断减少;另一方面美国黄金储备不断增加。除非采取进一步的货币紧缩政策,英国将无法维持1英镑兑换 4.86美元的汇率(同时也意味着英国政府无法维持原定的黄金-英镑平价)。其实,英国在恢复金本位的时候,把英镑的含金量定的低一些(对美元的汇率定的低一些),情况可以会有所不同。但教条主义的英国却认定:维持英镑原有含金量不变是金本位应有之义,不肯改变英镑的含金量。黄金储备的减少迫使英国在1931年宣布放弃金本位。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退出金本位,世界进入了无序的竞争性贬值时代。大国之间的“以邻为壑”的贸易和汇率政策大大加剧了1929年-1939年的“经济大萧条”。
布雷顿森林体系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基本特征,是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制和固定汇率制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议条款,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其波动幅度上下不得超过百分之一。而美元同黄金的兑换比率则固定为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其他国家货币同美元而不是同黄金直接挂钩,可以用美元储备代替黄金储备,从而缓解了这些国家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只有在当其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失衡” (fundamental disequilibrium),并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准之后,才能实行货币贬值。对什么是“根本性失衡”,并没有明确定义。一般的理解是,如果国际收支不平衡已无法通过调整国内政策加以纠正,国际收支不平衡就是根本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对国际收支暂时失衡的当事国提供信贷便利,以尽量减少贬值的必要性。各成员国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把一定数量的黄金和本国货币存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帮助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成员国从基金借款(通常是借美元)时必须以本国货币交换,然后再在三、五年之后用美元将其买回。一般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是特里芬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是国际贸易中唯一的交易媒介、结算工具。为了满足国际贸易的需要,美国必须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足够的“美元流动性”。1960年,比利时经济学家特里芬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能否维持取决于海外美元持有者对美元的信心,更确切地说,取决于他们对美国政府能否履行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承诺的信心。但是,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将随国际贸易量的增长而增加,而黄金产量的增长却是有限的。这样,海外居民美元持有量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比例将越来越高。这种趋势最终将动摇美元持有者对美国政府遵守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承诺的信心,进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特里芬关于黄金储备不足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预言从根本上是正确的,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的实际路径与特里芬的预期并不尽相同。事实上,随着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出口竞争力的提高,美国货物品贸易顺差减少,而服务贸易逆差(包括海外军事开支)则持续增加。在经常项目顺差逐渐减少的同时,美国的资本项目(政府海外贷款、海外援助和私人资本流出)始终维持逆差,而且大于经常项目顺差。国际收支状况的不断恶化迫使美国不得不越来越多的依靠输出美元来平衡国际收支。战后的“美元荒”变成50-60年代的“美元过剩”。可见,最终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因并非特里芬所预言的贸易增长导致的美元供给相对黄金供给增长过快,而是美国的持续国际收支逆差导致的美元泛滥。
美国的持续国际收支逆差说明美元高估。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初,在非官方市场上黄金的美元价格持续出现上涨趋势。投机者在官方市场出售美元购买黄金,在非官方市场出售黄金购买美元以牟取价差。1949年底美国黄金储备超过对外国短期负债(包括债券和证券)的数额为182亿美元;而到1958年底,上述数额不足50亿美元。从1950年至1957年,美国黄金储备平均每年减少13亿美元,仅1958年就减少了近30亿美元。随着美元对黄金贬值预期的加强,投机者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1948年,美国拥有全球货币储备的2/3。到1960年底,美国黄金储备额下降至194亿美元,而包括短期和长期在内的对外流动负债为189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尚能弥补外国机构和私人对美元兑换黄金的需求,但两者之间的差额只有5亿美元。到1970年,美国黄金储备进一步降至145亿美元,同期美国对外流动负债高达402亿美元,其中仅短期流动负债就已超过了黄金储备,达234亿美元。1971年,相对于外国官方和私人分别持有的400多亿美元和300多亿美元,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只有100多亿美元。1971年8月法国已经把92 %的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同年8月英国政府要求美国财政部把价值30亿美元的黄金从诺克斯堡转移到美联储在纽约的金库。面对黄金储备的急剧流失,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黄金窗口”,撕毁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布雷顿森林体系轰然倒塌。
第二是国际收支失衡纠正机制失灵问题。作为最后手段,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失衡”时,对汇率进行调整,以恢复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调整幅度仅为1%。在金本位制度下,国际收支失衡可以通过黄金的跨境流动得以调整。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只能由当事国采取紧缩或扩张货币政策加以纠正。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目标往往同国际收支失衡国的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相矛盾。
例如,1962年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曾建议美国把美元贬值到70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遭到肯尼迪总统拒绝。肯尼迪认为这将释放美国经济状况不佳的信号,但他同时也不想采取紧缩政策。1960年后期国际收支平衡恶化,与此同时美国的就业和通货膨胀形势也在恶化。为了减少国际收支逆差,美国本应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如升息),而其他国家则应采取货币扩张政策。但美国各界已形成充分就业(失业率不超过4%)是最重要政策目标的共识,美联储难于实行紧缩政策。美国也尝试通过资本管制抑制资本外流。例如,1963年美国开始征收利息均等税(IET)以阻止美国居民在海外购买金融资产。在尝试过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或代价太大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选择了美元贬值。先是美元对黄金贬值7%,而后各国汇率波幅的允许范围扩大到2.5%。1973年3月,各国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终结。
第三是戴高乐问题。法国总统戴高乐指出,建立在任何单个国家货币基础之上的货币体系都是危险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被自动视为等同于黄金。戴高乐认为事实上的美元本位使美国可以过上入不敷出的生活(to live beyond its means),并强迫欧洲国家为美国承担建立海外军事帝国的费用。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于美元几乎是唯一的可以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充当交易媒介、结算手段和价值贮存的货币,其他国家都不得不持有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这样,美国就可以印刷“借据”换取外国资源,而不用担心外国会使用这部分美元,即凭借这些“借据”向美国索取产品、劳务和金融资产。换言之,作为向全球提供流动性的交换条件,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美国向全球征收铸币税。
如果各国增持的美元储备同国际贸易增长相对应,应该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美元的国际购买力不会下降。在1960年代初期,美国物价水平相对稳定。1960年至1965年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了6.54%。但是在19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越南战争、约翰逊的“伟大社会计划”,美国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物价开始加速上涨。1965年至1970年间,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增加了23.07%,年均上涨4.25%。美元国内实际购买力下降意味着美元对黄金和其他国家汇率的高估。海外居民持有注水的美元意味着他们还要向美国缴纳通货膨胀税。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美国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马歇尔计划等)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流动性的。但随着经常项目由顺差转变为逆差,美国开始通过增加负债来提供流动性。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鲁夫(Rueff )借用裁缝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解释了这种变化的实质:
“如果我的裁缝(顺差国)希望和我(美国)达成协议——只要我把买衣服的钱付给他,他在当天就会以贷款形式把钱返还给我——我是不会反对从他那里订制更多衣服的。”
这样,裁缝(顺差国)不断为客户量体裁衣,积攒下越来越多的借条;客户(美国)为了得到新衣服,唯一要做的事情是开借条。这些借条最终能够兑现什么?兑现多少?没人知道。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一个 “没有体系的体系”,即“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体系。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三大特点:第一,多种国际储备货币并存,但美元依然是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第二,多种汇率制度并存,但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第三,资本自由流动,但不禁止实行不同程度的资本管制。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根本特征是美元本位(不是黄金-汇兑本位制)。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不再有黄金支持。对外国持有者来说,美元仅仅是由美国政府开出的、以国家信用担保的借条(“IOU”)。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有黄金支持尚且崩溃,同黄金脱钩后,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美元为何依然能够充当本位货币呢?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非是市场对美元的不信任票、而是对美国政府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承诺的不信任票。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投机空间大幅缩窄,特里芬问题消失。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尽管美元对黄金的价格剧烈贬值,美元对其他货币的贬值则相对温和,且有双向波动。这说明,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本身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动摇。尽管美元不再有黄金的支持,但由于有强大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美元信用并未丧失。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跨境资本的狼奔豕突,各国之间的双边汇率变动频繁且剧烈,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国际收支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发生频度大大超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全球贸易得到迅猛发展,全球金融一体化大大加强,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虽然明显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增速,但全球经济毕竟并未发生金本位下的长期衰退。因而,尽管有种种不满,但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合理性并未遭到过根本性挑战。
现阶段国际货币体系弊端与中国定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结束了这种状况。2009年联合国授权建立的“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指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三大缺陷:通货紧缩倾向、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而这些缺陷的根源则是:作为一种国别货币的美元充当了国际储备货币。
所谓通货收缩倾向是指,为了避免经常项目逆差导致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非储备货币国往往要积累相当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外汇储备的积累,意味着购买力的“冷藏”。如果经常项目顺差国不相应增加支出(这意味着经常项目顺差的减少甚至经常项目逆差的出现),全球的总需求就会因经常项目逆差国的单方面调整而减少,全球经济就会陷于衰退。
所谓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机制缺失是指,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资本的自由流动实际上抵消了汇率调节机制的作用。特别是短期投机资本的跨境流动更是给国际收支的平衡带来很大不确定性。以美国为例,自1980年以来美国几乎每年都是经常项目逆差,但是,美元汇率在更大程度上却是由资本流动的方向决定的。当美国国内利息率较高之时,尽管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由于资本的流入,美元往往不但不会贬值,反而会升值。汇率错位(misalignment)可以长期存在。
所谓不平等是指,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浮动汇率制度下,非储备货币国必须积累大量外汇。持有外汇资产仅仅能得到很低的回报。非储备货币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大量积累外汇储备的造成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极大不平等。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对美国支付铸币税。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者在早期声称,实行浮动汇率之后,各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会降低到最低限度。当充当交易媒介和结算手段的“国际流动性”不足的时候,一国可以从国际货币市场借到足够的美元,只要借款国有足够的资信。但亚洲金融危机彻底证伪了这种观点。由于资本流动的“逆周期性”,发展中国家越是需要美元流动性,就越难于得到美元流动性。在后布雷顿森林时期,全球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的1970年,全球外汇储备仅为450亿美元,1979年上升到3000亿美元。从1973年到1979年, 全球外汇储备的增速为17%,明显高于1960年代的9%。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预防投机资本的攻击,作为一种保险,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不得不大大增加美元外汇储备的积累,这些美元储备已经同满足“国际流动性”需求毫不相干。1990年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对GDP之比为5%,201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30%。202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高达12.7万亿美元。 在外汇储备中,美元外汇储备的比例在1999年高达71%,2020年是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最低值,但依然高达59%。无论积累外汇储备的目的是什么,其结果都是使发展中国家浪费了大量本应该用于消费和投资的实际资源。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美国消耗了大量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实际资源,却不用担心还本付息。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问题是,一方面,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完全靠信用支撑的美元是本位货币,或者如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 “锚”;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2023年美国国债占GDP之比将达到103%,超过二次大战以来的峰值;到2050年这样比例将达到250%。国债的持续增加将使美联储难于改变低利息率政策,而低利息率政策又使美国难以改变已经持续近50年经常项目逆差状态。经常项目逆差的长期累积使美国的海外净负债超过14.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67%左右。这一比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将继续增长。与此相对照,在1960年代末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时候,美国是净债权国。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的近50年中,鲁夫的裁缝并不在乎日复一日地给顾客缝制衣服,尽管所得到的仅仅是客户开出的借条,裁缝对客户是否能够最终还钱似乎并不在意。而顾客则落得享受不断得到新衣服、而无需操心把借条变成“真金白银”-偿还债务-的好日子。裁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要求客户把借条“变现”为实际资源?裁缝的超强耐心可以说是当代金融的最大难解之谜。
应该看到,中国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中国其实就是鲁夫比喻中的那位超级耐心的裁缝。中美之间关于贸易不平衡之争,很像是一幕荒诞剧:一方面是我要把钱借给你,而且情愿不收(或少收)利息;你不肯借,但我偏要借给你。另一方面是我想借钱,但偏说我不想;而且说你把钱借给我是害了我。美国政客表面抱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私下却乐得看见中国购买美国国库券以积累外汇储备。
十几年来,我曾不厌其烦的引用美国前总统办公室主任,现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主任Phillips Swagel 先生对这种奇怪现象的解释。他的解释虽然是针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但却点破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维持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积累美元外汇储备的真实思想。Swagel先生说 :
“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下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也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率。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只付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了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
Swagel先生接着说:
“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的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一个有心计的人(a cynic)可能会希望(实际情况是):压中国升值不是(美国政府)对不明智政治压力的回应,而是一种狡猾的图谋(devious attempt)。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使美国的好日子得以延续下去。”
顺便说明一下,我本人认识Phillips Swagel先生,我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客观说,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早已是千疮百孔。没人知道一辆年久失修的破车可以继续走多远。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他们没有选择,只能一直留在车上,直到车辆倾覆。
而中国不是这些大多数国家的中的一员,中国有自己的选择。在过去数十年中,特别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和周围邻国就开始了种种尝试,但这些尝试都无果而终。2009年后中国开始走自己的路,但很快就发现没有道路是平坦的。高海红教授的新著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中国和邻国已经走过的曲折道路。但是,正如高海红教授在她的新著中所表明的,面对畏途巉岩,只要中国坚持尝试下去,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坦途。
居安思危,为国分忧,国际金融学者责无旁贷。预祝高海红教授在探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研究道路上取得更大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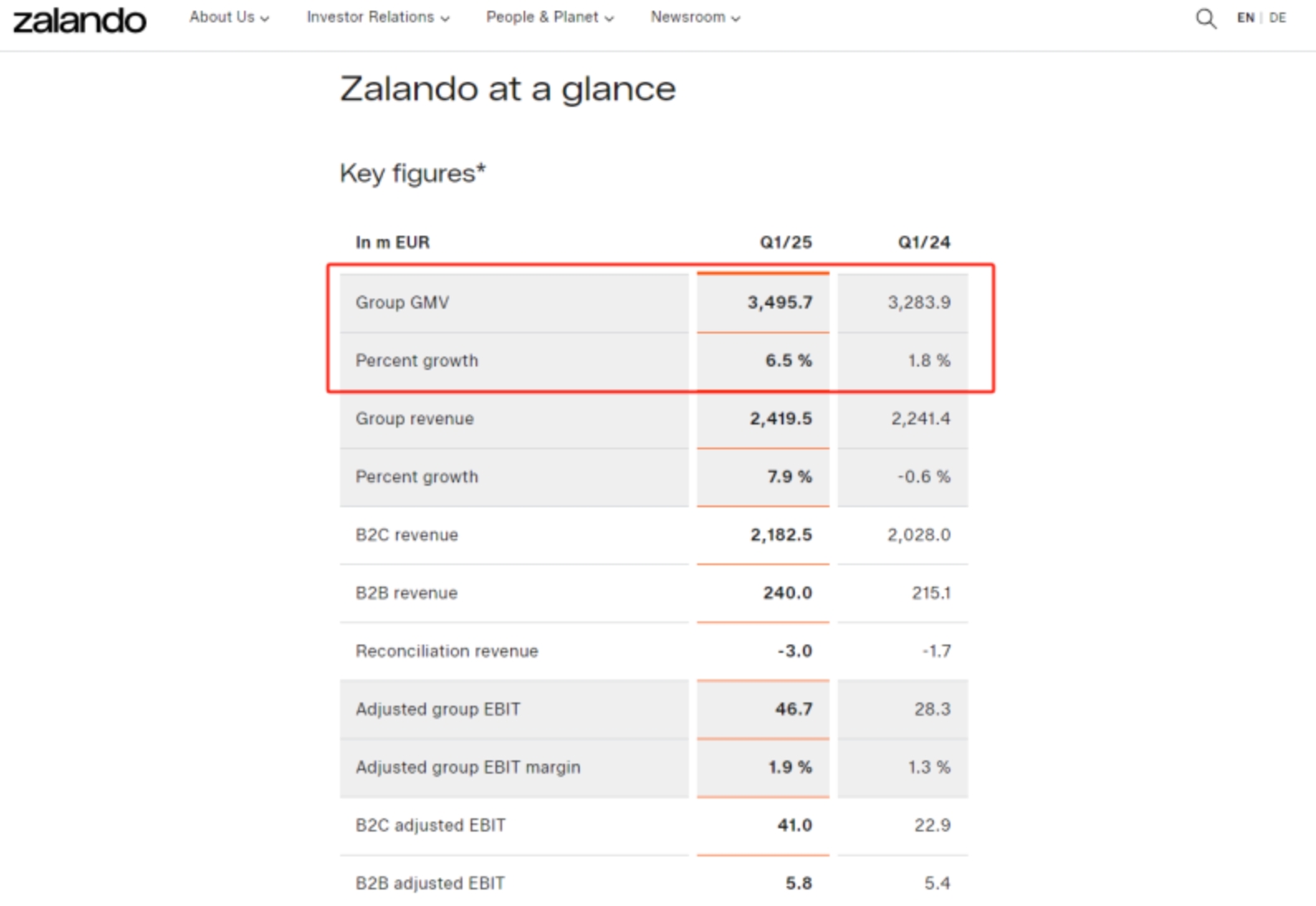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