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有思资本”)
同富裕话题一出,有人又回忆起改革之前的年代。
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那是一段贫富差距很小的时光,虽然不富裕,但大家都差不多。而贫富差距拉大,则是市场经济造成的。
反对者则争辩说,那时候贫富差距小,但并不意味着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因为当时的分配方式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误区,这就是:共同、共同、共同。对于改革前中国的收入分配,人们经常用两个词来表达:平均主义、大锅饭。以为那就是共同贫穷,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记得在1988年或1989年,在一本似乎叫《国情研究》(那本杂志好像只出了一期)的杂志上,我曾经发表过一篇短文。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把改革前分配体制界定为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做法。如果说当时是大锅饭的话,也不是一锅,而是几锅,而且,大锅之外还有小锅。
说当时是大锅饭、平均主义,没有错。比如,当时全国同样级别的干部、工人工资都是一样的(地区间有一些差别),没有奖金,干好干坏一个样。全国的大学生,毕业时的工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并且会固定很长时间(因为当时工资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冻结状态)。没错,这当然是大锅饭,是平均主义。
但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在另一面,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景象。也就是说,就是在大锅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的同时,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也是明显存在的。
这个不平等存在于诸多的层面。首先,是特权的存在。杨奎松教授指出,当时的工资实行的是官阶差序标准,同时把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的分配等级。其级别的差距是很大的。而且,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这尤其体现在实物分配,特别是住房分配以及稀缺资源的配给和获得上。
其次,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平等。据世界银行的计算,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是2.5, 比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要高(平均约为1.5),稍大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平均约为2.2)。在那个时候,一些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是低得可怜,甚至连基本温饱都无法保障。更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些列制度安排,城市居民和农民成为两种事实上的等级身份。
再次,在城市中干部和工人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这不仅仅表现在工资收入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实物分配和社会福利上。比如,住房的分配和补贴、医疗待遇、子女教育和就业等等。而在农村内部,也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
因此可以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的社会;微观上是平均主义的,宏观上是不平等的;由个人视野感受到的是平均主义的,宏观数据展示出来的是高度不平等的。这也是人们心目中平均主义或平等印象形成的原因,因为更大范围的不平等是在你狭小的视野之外。实际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普遍贫穷的存在,你可以看看哪个贫穷的国家是普遍贫穷的?往往越是贫困,其贫富差距越大。
将一个平均主义与不平等并存的社会想象或感受为是共同贫穷的,会产生一系列有害的误导。首先,有些底层人会愤世嫉俗地想,与其贫富差别巨大,你富我贫,不如消灭富的,大家一起贫穷。实际上,共同贫穷比共同富裕还难以实现。共同贫穷的想象和追求,在结果上带来的往往是贫困基础上的两极分化。
更现实的误导是,改革方向的定位出现一定的偏差。从形成激励机制以促进经济发展来说,首先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无疑是应该的。但由于将改革前分配上的弊端简单界定为平均主义、大锅饭,就只顾破除平均主义,而忽略了解决事实上存在的巨大不平等、不公平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已经有很大进展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理应同时解决平均主义和不平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通俗一点说,就是既要解决锅内的平均主义的问题,也要解决锅际的不平等问题。但由于当时的判断出现了偏颇,导致改革只强调了破除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问题,只强调了拉开收入差别的必要性,而忽视了解决不平等问题。结果使这方面的问题不断积累,日益严重。
理论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有时甚至比想象的更残酷。如果我们将发展与贫富差距做个组合,也许可以形成下面的排列:经济较快发展+温和贫富差距、经济较快发展+贫富差距巨大、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贫富差距较小、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贫富差距巨大。如前面所指出的,其中第三种在现实中是很难做到的。有人期望,在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情况下,实现共同贫穷也好?可以不客气地说,您想多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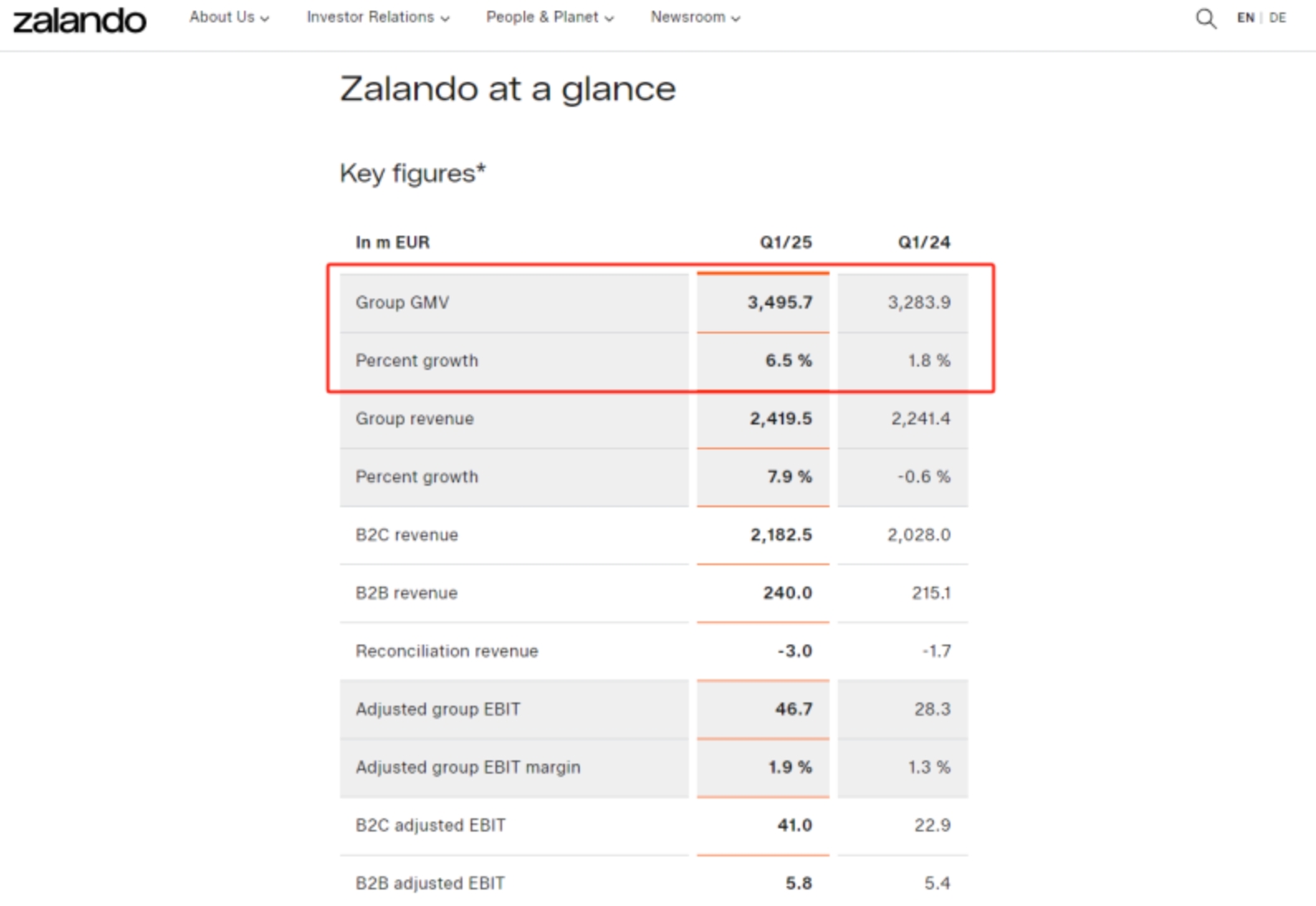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