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能够跨时代的技术红利。
1984 年,Neil Harbisson 出生于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因为他患有全色盲(achromatopsia),七彩世界在他眼中犹如观看黑白电视一般。2003 年,他遇见计算机科学家 Adam Montandon 并且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Adam 等人在他大脑中装了一个“电子眼”——一个光波频率到声波频率的转换装置,从此在 Neil 的意识里,红色、黄色、绿色都可以由一段不同的声音呈现,他也因此“听到”不同颜色。慢慢地,他发现这个电子眼成为了五官的延伸,融进他身体里,成为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后来,Neil 成为一名艺术家,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半机械人”。
在当时没有埃隆·马斯克们的“布道”之下,人们还没有深入理解脑机接口是怎么一回事。直到 Neuralink 动作频频,最近一段猴子仅用大脑“意念”控制屏幕光标玩游戏的视频放出。
要知道被马斯克送进实验室的猴子并不是第一只。早在 1969 年,神经学家 Eberhard Fetz 训练猴子利用思考活动触发神经元,启动了连接神经元的仪表盘,完成第一个真正的脑机接口实验。然而接下来的四十年,脑机接口都是一项极其前沿的技术。直到近几年,在马斯克们相继成立一批脑机接口公司之后,这项技术逐渐开始从实验室踏入商业世界。
还不能落地的脑科学,为什么值得关注?
今天人们可以简单理解脑机接口的意义,在大脑和外部机器的连接之下,一方面,生物体内的数据可以被捕捉到,我们不仅可以知道人体更多的秘密,也可以实现大脑信号对于外部机器的控制;另一方面,大脑接受的外部信号,进而对人体产生干预和影响。
脑机接口只是广义脑科学之下的一个研究分支。由于研究难度不亚于探索宇宙的黑洞,因此脑科学被称为“人类科学最后的前沿之一”,是我们理解自然现象和人类本身的“终极疆域”。对于脑科学,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一体两翼”的布局建议,通俗来说,就是先把大脑结构和如何工作搞清楚之后,更好地预防和诊治重大脑疾病,以及利用大脑运作原理及机制推进类脑人工智能的开发。
这一战略部署被看作是脑科学领域往前发展的指示灯。脑科学开始成为一个创业赛道,有越来越多的公司进入布局。医疗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脑科学研究最先落地的产业方向。
在诊断方面,优脑银河可精确量化全脑 200 多个功能区,得到个体化脑功能图谱,为之后临床质量提供基础。此外也有慧脑云、脑陆科技等脑科学服务提供商在 AI 辅助影像学、脑电图诊断等领域展开布局。在临床治疗上,还有提供手术辅助机器人的公司。
当然也有许多公司将应用场景拉得更广。他们关注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认知障碍病人等大脑认知功能缺陷,以及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甚至需要改善记忆功能的青少年群体。比如 BrainCo 就推出能够检测学生注意力的头环,就像锻炼肌肉一样锻炼大脑,通过神经反馈训练达到提升学习效果的作用。
当前全球有超过 5000 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3.5 亿抑郁症患者……即便脑科学还是人类认知的“黑洞”,但是并不影响它已经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近期一则公益短片,将这个话题再次拉入我们的视野。
不少公司表示,他们是科研和产业两手抓。多数脑科学领域的创业公司还处于非常早期的融资阶段,虽然脑科学早已不是高高在上的虚无,但远未到产品成熟和大规模商业化阶段。这也印证,脑科学的大厦尚未建成,需要更多基础理论研究来夯实地基。
2011 年,IDG 创始人麦戈文先生和 IDG 资本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建设的 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相继成立,其中清华大学聚焦将最先进的工程科学技术应用到脑科学研究,北京大学专注于心理、认知、神经科学、精神疾病等相关多学科的联动;北京师范大学偏向于神经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脑发育等。十年间三所高校在脑科学基础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理论成果。
比如清华大学姚骏研究组在《PNAS》发表合作论文报道双相情感障碍发病机理的研究进展。北京大学周晓林课题组在 Cerebral Cortex、NeuroImage 发表文章,在内疚情绪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北师大在自闭症儿童神经反馈注意训练、儿童特定领域学习训练方面也取得多种奖项认可。
继 MIT 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诞生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后,国内这三所脑科学研究机构某种程度上也被赋予了类似期待和意义。
虽然这些基础研究成果在短期内还不能变成直接落地的项目,但其潜在的技术红利已经隐现——据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大约有 10 亿人口患有脑疾病,脑疾病占全球所有疾病负担的 28%,中国有超过 5400 万人患有抑郁症,脑科学研究应用落地的需求广阔且急迫。
寻找新的技术红利,要往科学一端布局
押注基础科学研究——这种看起来像给科学究研做公益的事情,越来越得到“大佬”们的关注。比如前不久辞任董事长的黄峥,捐赠一亿美元设立了繁星科学基金,打算做生命科学和食品科学方向的研究。
类似地,马云、马化腾、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及其夫人,都是“生命科学突破奖”基金捐助人,该奖项旨在激励那些从事对抗癌症、糖尿病、帕金森和其他疾病研究的科学家。陈天桥,放着好好的游戏业务不做,去做今天看不到什么商业价值的脑科学研究——他斥资 10 亿美元推动脑科学研究,到硅谷的两年时间里见了近 300 个教授。
还有即将卸任亚马逊 CEO 的杰夫·贝佐斯,在他作为 CEO 的最后一封致股东信里,他强调“创造”价值对于企业来说的重要性——因为企业要做的不仅仅是把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而价值创造的根源是什么?就是“发明”。所以自称“发明家”的贝佐斯直白地表示自己要多花时间在蓝色起源以及火箭技术上。
从国内到国际,都可以找到对基础科学研究情有独钟的案例,背后有何共性原因?
或许我们可以在黄峥的致股东信中找到一些答案,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甚至异化让其意识到这种传统的以规模和效率为主要导向的竞争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要改变就必须在更底层、根本的问题上采取行动,要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础理论上寻找答案。
换句话说,在原有的技术红利上实现变现这件事会越来越难。中国企业想从“贸工技”走向“技工贸”,只着眼于眼前的技术红利是不够的,需要构建新的技术红利,这就要求再往前,也就是在科学一端布局,促进科学向科技的转化。
回到开篇提到的例子,从第一个脑机接口实验,到这项技术走入商业世界,经历了四十年。同样人工智能首次提出是在 1956 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互联网始于 1969 年美国的阿帕网……这些如今被广泛应用的技术经过半个世纪的基础理论积淀才逐渐引爆,为商业世界创造价值。
不仅是科技公司,资本机构也越来越提升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重视程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IDG 资本,其在很多前沿技术上的布局都远早于风口的到来。
近日其在脑科学这一前沿领域就动作频频——在 4 月 22 日宣布再次对清华大学-IDG/麦戈文脑科学研究院进行捐赠,并承诺将持续通过捐赠助力中国脑科学基础研究,捐赠金额预计每年不少于 2000 万人民币。
其他前沿技术布局方面,以近两年才爆火的芯片行业为例,IDG 资本早在 2002 年便已经涉足。其在当年参与了芯原股份的 A 轮融资,此后又先后在芯片设计、传感器、集成电路、半导体设备等多个领域投资了 10 余个细分行业的头部项目。同样的前瞻性布局还体现在新能源赛道——从 2007 年起,IDG 资本便在太阳能行业开始投资布局,投资了包含爱旭股份、钧石能源、昆兰新能源和天华太阳能(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在内的多家行业领先公司。此外在医疗、智慧出行领域,IDG 资本都展现出了长期关注、持续陪伴的特质和优势。
IDG 资本创始董事长熊晓鸽说,从做投资角度看,大约每十年左右会有一批主导技术。像投资 PC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机构们会重点关注企业的商业模式、执行和管理能力等。而针对于技术投资,不论投资脑科学还是自动驾驶、生物工程等等,创业者已经不同,大部分是研究出身,企业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含量与技术门槛比较高。相应的,做投资也需要懂技术。
在脑科学领域,过去 IDG 资本通过在基础研究上突破带动临床医学发展,这一次 IDG 资本邀请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徐立以理事身份参与到清华大学脑科学研究院的相关工作。从市场需求出发,给技术创新带来新的思路。
“在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研发是个费时费力、成本高昂,而且成功率极低的工作。但是基础研究往往能够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科研水平的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社会现实问题的改善发挥根本性的作用。”熊晓鸽说。
当你无法搭着别人已经建好的地基往前走,就需要在前期有足够长线的投资,依靠自己创造红利,这样才会在未来对社会有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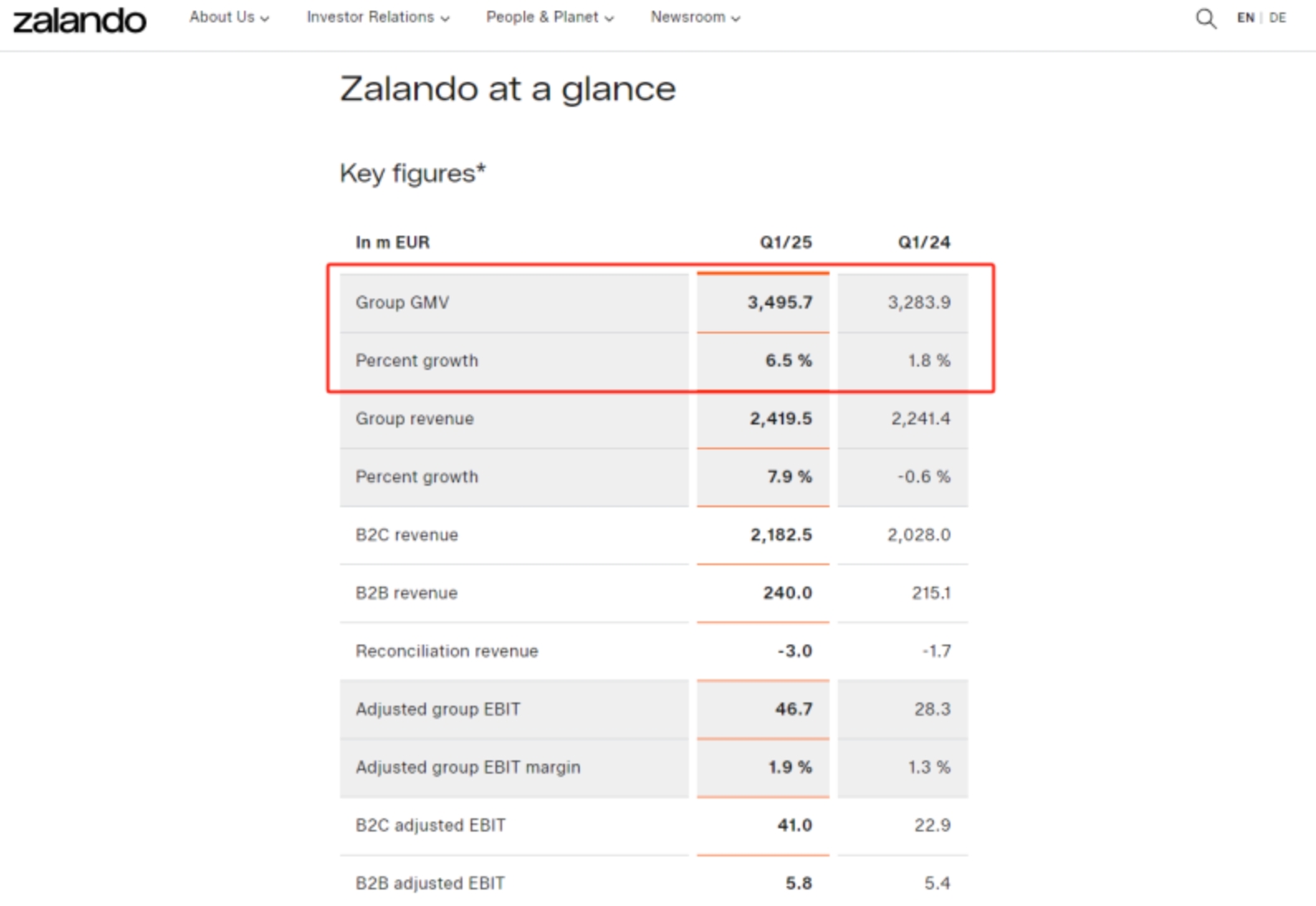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